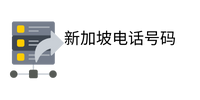下一届 ECF 日的主题是“我就是我说的”,这是否只适用于精神病确定性?无论它们是由分析师解释还是推断的,诊所都充满了神经症患者词典 [1]的例子 是她 。让我们以多拉的案例为例,弗洛伊德在五种精神分析中研究过这个问题,而拉康在《转移干预》中重新解读了这个问题,其中“我是”的不同表达遵循辩证的逆转,并导致对无意识越来越清晰的肯定。
在《移情干预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:“精神分析是一种辩证的体验 [2],当我们追问移情的本质时,这一观念必须占上风” [3]。本文在本卷中延续了“逻辑时间和预期确定性的断言” [4],其中已经宣布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的辩证运动的思想。
在《对移情的干预》中,针对朵拉的案例,拉康提出了三次辩证逆转。
第一次:多拉提到了令她难以承受的抱怨,可以总结如下:“我父亲和K夫人已经相恋很久了,他们请我照顾孩子,以便他们可以秘密见面。”这里理解的字典是:“我是我父亲和K夫人交换的对象。 “。弗洛伊德的干预:“看看你在你所抱怨的混乱中所扮演的角色” [5]带来了第一次辩证逆转。
从此时起在第二阶段
朵拉的参与以及她与由她父亲、 K夫人、MK 和她自己组成的四对方舞团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显现。证据是,杜拉的父亲送给K夫人的礼物——为了弥补由于阳痿而无法进行性关系的缺陷——让 MK 将注意力转 移 阿塞拜疆电话号码库 到杜拉身上;杜拉的父亲也送给母亲的礼物,以做出“光荣的补偿” [6],正如拉康所说。这里,我们推导出字典里的说法 :“ 在他们这段关系中,我是帮凶 。”
第三次强调,让年轻女孩感兴趣的不是父亲和K夫人的 集思广益并整理广泛主题 关系,而是她的嫉妒掩盖了她对这个拥有白皙迷人身材的女人的兴趣。所谓因这位家庭朋友而产生的竞争只是一个谎言。多拉心满意足地参与了交流。这就是他忠诚的原因。
第三次辩证逆转揭示了K夫人
对于朵拉在回应女性气质之谜时所具有的真正价值。 在分析该案例的第二个梦时,弗洛伊德 将她寻找路的“两个半小时 ”与她在博物馆圣母像前度过的两个小时联系起来。拉康说,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,而是一个谜团 线数据库 的问题,“是一个人自身的女性气质的谜团” [7]。因此,我们来谈谈本案例中“我是”的第三种情态:“我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年轻女子,我无意识地问自己一个问题:什么是女人?通过另一个女人。”
这种治疗的过程是从对潜意识的否定——“ 看看他们让我经历了什么…… ”——到对它的肯定:“ 我陷入了我所谴责的不幸,因为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,影响了我的享受 ”。
对这一原发病例的检查使我们推断,如果在精神病中“我就是我说的”可以呈现出不可动摇的确定性,那么在神经症中,最初的词典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遵循辩证的逆转,因此其固定性较低。这揭示了与存在相关的词典的脆弱性。在《孤独一人》 [8]中,雅克-阿兰·米勒提出了本体论存在的弱点,以解释说话的存在。如果我们试图探查主体在存在中的位置,将其理解为言语存在与其享受方式之间的关系,那么我们就会找到更坚实的指南针。这更像是一个饮酒学的问题,也就是说,这是关于那些独自坚持某一主题并解释其享受的人们的问题 [9]。